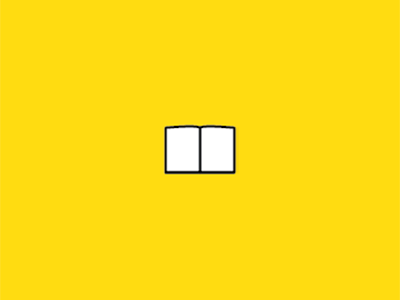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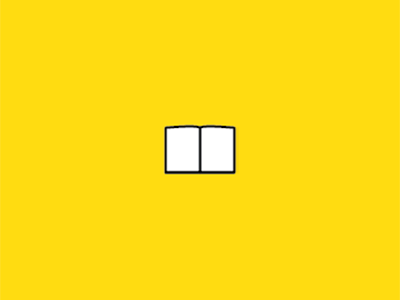
前面系列文章所述,尤塞氏患者的症狀可能會影響到視野、夜間視力、以及聽力、平衡。但是分型、疾病相關基因變異的不同,導致症狀嚴重度、出現時間、惡化速度不同。這些症狀,懷疑或檢驗確定的疾病相關基因變異、以及會逐漸惡化的病程現實,或多或少,對患者的生活種種、身邊人際,造成一定的衝擊。
尤塞氏患者,如果出生即伴隨聽力異常,直接影響到的方面是語言溝通、社會互動關係的發展。在早期新生兒聽力篩檢未普及時,若聽力損失未及時發現,則可能會誤以為小孩個較為安靜,而錯誤地忽略潛在的徵兆。**由於不均勻的聽力頻率損失,較慢配戴聽力矯正輔具的孩童,可能會較正常人慢開始學會語言溝通,以及學習到錯誤的發音方式。這將對未來的發展、教育、社會互動的形成有負面影響。**所幸在台灣,新生兒聽力篩檢逐漸普及後,絕大多數先天聽力損失的新生兒,可以透過醫療院所專業團隊早期發現、及時介入,而將影響降至最低。
在眼睛方面,由於一些尤塞氏患者的眼睛相關症狀(夜盲、視野狹窄),從青少年甚至成年後才慢慢顯現,患者在身體發展以及社會適應中,會經歷一段漸漸衰退,以及向環境互動漸漸適應的交互,但由於其他感官的補償,患者難以察覺眼睛部分的問題,甚至有可能將注意力不集中、跟不上環境訊息歸咎至近視、聽力損失等較明顯的原因。「溫水煮青蛙」不外如是。
**夜盲、視野狹窄的症狀影響到患者生活中的廣泛層面。**由於夜盲的表現是光線低於一定亮度後,所有眼前所見事物一概不明,而視野狹窄則讓患者對周遭事物容易視而不見,近在咫尺才會有所察覺,**故患者日常行動有一定受限,尤以夜間為甚。**人多的地方如鬧區、景點,交通巔峰忙亂之處,由於容易碰撞到人、發生擦撞意外,有些患者會下意識避開、避免獨自駕駛交通工具;逛夜市、演唱會、以及電影、夜唱等台灣流行的夜間娛樂,由於夜間視力的受限,對許多患者來說並非是可以放鬆享受的活動;親近大自然的消遣,觀星、賞螢火蟲、月下酒酌,更是對患者來說可望而不可得的世界。
一個較容易被忽略的現象是光暗適應能力較弱,縱然不到夜盲般完全看不見的地步,但是患者從室外走入室內,或者從室內往光亮的外頭走出去,會有調整時間比正常人長的狀況。患者需要一定時間,等待新環境在眼中的亮度慢慢顯現正常,才有辦法繼續行動。舉例來說,在夏天日正當中之時驅車進入地下停車場,會有一段時間看不到,此時對患者來說有一定程度的不方便及危險。
與聽力障礙加乘,為了迫使自己跟上環境的步調,患者有時會緊張、焦慮。雪上加霜的是,若將注意力視為一種有限資源,則該項資源在無法放鬆的狀況下將更快耗盡,對患者的身心是一項潛在的折磨。
有人說,即便有聽力輔具,聽力障礙者,與現實世界,仍然有那麼一點隔閡。**這個隔閡來自於即時溝通的不便、於外界訊息的不敏銳,以及認知到自己聽不清楚的現實,而對自身存在、對外在世界連結的不安與焦躁。**由於人類發展過程中常由與他人、社會的互動經驗中,參照且形塑一部分的自我。縱然人呈現出來的性格極端複雜,先天及家庭教養的因素難以預測,不良的外在互動回饋經驗,或多或少可能帶來一些特質,如畏縮、低自尊、或他人難以理解的易怒情緒等。
承襲聽力障礙的經驗,與眼睛問題等聯合,尤塞氏患者在大多數正常人環境裡,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,容易因為不符合社會禮俗、或既定情況下的正常反應(他人打招呼沒有注意到而未回應、說話因自覺太小聲而聲量越來越大對他人形成壓迫、走路容易撞到人、在狹窄空間未主動讓路),而出現有意或無意的排斥。這些排斥不見得充滿惡意,而是正常人類群體、生物的本能作用。但承接這些排斥感的尤塞氏患者,容易將這些感覺放大,而銘刻成傷痕般、耿耿於懷的負面經驗。
由於外觀看起來幾與正常人無異,加上疾病罕見以及初期症狀輕微,而相關醫療資源沒有早期辨認出的延遲,導致功能慢慢受影響而不自知,尤塞氏患者可能過度努力,以正常人的身份想融入這個社會,傳統人要有所用、上進的價值觀氛圍,則可能加重了患者處在夾縫,裡外不是人的複雜感受。
症狀顯現,患者、父母開始尋求醫療協助甚至遺傳諮詢時,也是另外一種掙扎。一個層面是,導致尤塞氏症狀的可能先天疾病相關致病基因,一旦揭明,在傳統觀念、婚育世界中將被貼上標籤,帶來的衝擊不僅只有患者本身,還有整個家族。完美或不完美?孩子未來的競爭力或低人一等?**近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現實,直接帶來更深、更無可奈何的無歸屬感。**而一旦經過專業醫療告知確診,在人生中重要階段,猝不及防得知眼睛病程將逐漸惡化的噩耗,對未來感到迷惘,對就業、能否自食其力的不確定感到恐懼,更是尤塞氏患者的深層焦慮來源。
尤塞氏患者在身體功能、人際社會及心理上,皆面臨著環環相扣的課題。但無論接受不接受疾病、接納不接納自己,尤塞式患者一生中都要與這些困境共存,跟正常人一樣,每天與名為現實的浪潮搏鬥。以同樣的普世價值對待,多一點明理、多一點善意,或許,對尤塞氏患者便已經是最大的救贖了。
2023.7.25 黃俊榕醫師 撰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