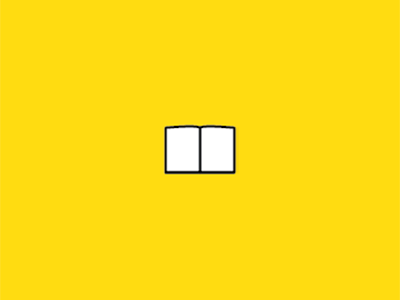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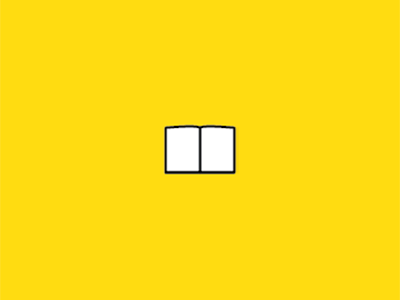
我1993年出生,今年30歲,2003年(10歲)確診聽障並配戴助聽器、2016年(23歲)經眼底鏡檢查診斷為視網膜色素病變、2020年(27歲)經基因檢測確診為尤塞氏綜合症。
父母盡心盡力扶養我與手足長大,但對於我的特殊情況他們缺乏經驗,小時候「口語發展慢」」認為是「文靜」、「呼叫沒有反應」認為是「專注」、「講話含滷蛋、大舌頭」認為是「可愛小朋友特質」、「走路走不好」認為是「肥胖所致」。畢竟障礙程度是輕度,對聲音還是有反應。直到上幼兒園,團體活動中要叫特定小朋友包含我時我沒有聽見,發生不少次老師怒氣沖沖地質問我怎麼不聽話,但小時候的我不知道問題,也不懂如何表達需求,於是恍惚又困惑地度過那些時光。
上了國小,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,我的座位在後排,發現上課時若是老師沒有用麥克風、聲音頻率又特別高的時候,雖然我聽得見聲音,但無法辨識內容。不過靠著自行發展的唇語能力、勤勤懇懇地閱讀還是能應付低年級學業。直到接觸兒童美語,發現閱讀及聽力的落差,父母才特別正視問題的嚴重性,在10歲的時候配戴助聽器。各方面如課業及人際互動表現平庸,年紀小時的確會因為擔心遭受異樣眼光而選擇低調,面對優秀的同儕會自卑、面對心儀的對象會退縮、因能力趕不上企圖心而感到無力、因不了解的指控感到冤枉,種種的情緒不斷堆疊、壓抑形成一種內耗型人格。但隨著年紀越大,不斷自我省思,逐漸能以坦然的態度面對自己的障礙,並找到平衡的方式。
大學時經常會和朋友看電影,直到有次電影已經開場,中途進去時我左碰右撞,反之我朋友迅雷不及掩耳地坐到座位上,那時開始懷疑自己夜視力比較差,但心中悄悄打個問號後仍擱置了。偶爾去旅行,旅伴可能望著天空說:「哇,好多星星啊!」,我往上看的瞬間只有瞧見北極星,多看了好幾分鐘才多找到幾顆,和他的滿天星星還是有不小的距離。隨著一些插曲認知到自己應該是有夜盲,但對於夜盲的境遇與處置沒有概念,認為不至於影響生活。
畢業後當了公務員,在學校單位服務,選擇了穩定的生活。有一天與當時交往對象到頂樓去吹風,頂樓沒有任何燈光因此我走得蹣跚,對方察覺我的異狀,我表示我應該有夜盲,我要察覺基本上都有賴於日常「與他人比較」,他聽得見我卻聽不見,他看得見我卻看不見,或是個人顯著退化。後來對方從論文平台同時搜尋聽障及夜盲關鍵字,發現有關「usher syndrome」的論文,依據論文回推我的表現,除了聽障及夜盲之外,對方想起我常常在無預期情況下,他若在眼角的不遠處向我招手,我會比一般人容易忽略,討論後我即預約了眼科檢查,檢查結果的確是「視網膜色素病變」,詢問醫師會不會是「尤塞氏綜合症」,醫師表示在有限的檢查結果下不能給予確定的答案,後來過了幾年終於透過基因檢測確定就是「尤塞氏綜合症」。
確診後,我開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,太陽下配戴太陽眼鏡,一般眼鏡會選用濾藍光鏡片,培養運動的習慣增強血液循環,建立固定作息盡量避免過度用眼。退化情況來說,聽損與小時候最初的數據相比大概退化5分貝,視力上則是眼周多了一些雜訊。一路以來,很幸運地遇到貴人。在我對於病症感到茫然的時候,藉由網路文章找到黃俊榕醫師,進而認識靖永皓教授及病友。除了更了解自身,心理上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。
2023.8.15 李宜蓁撰寫